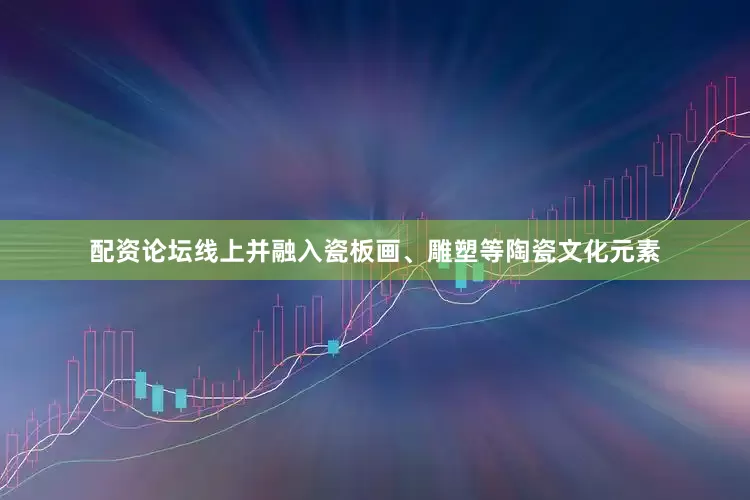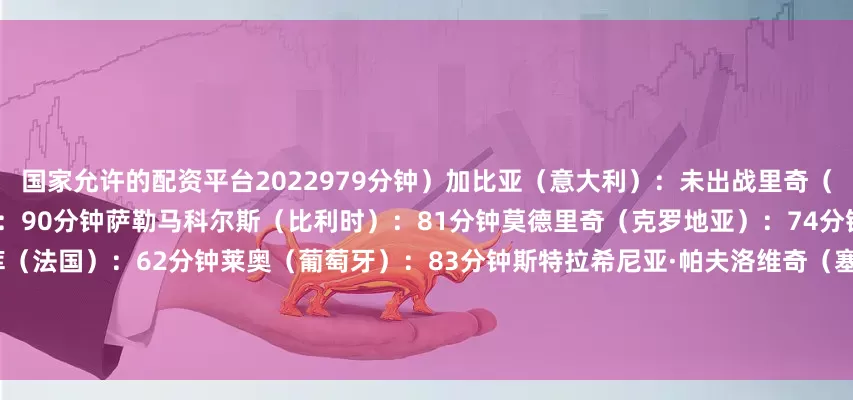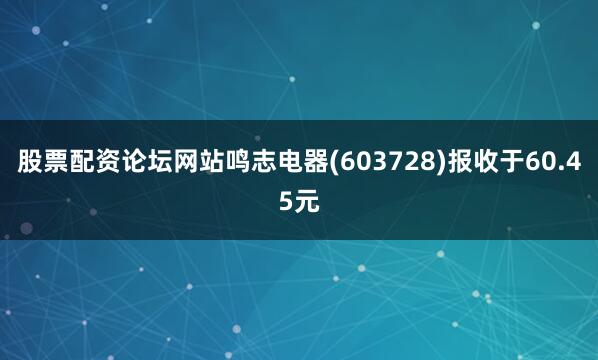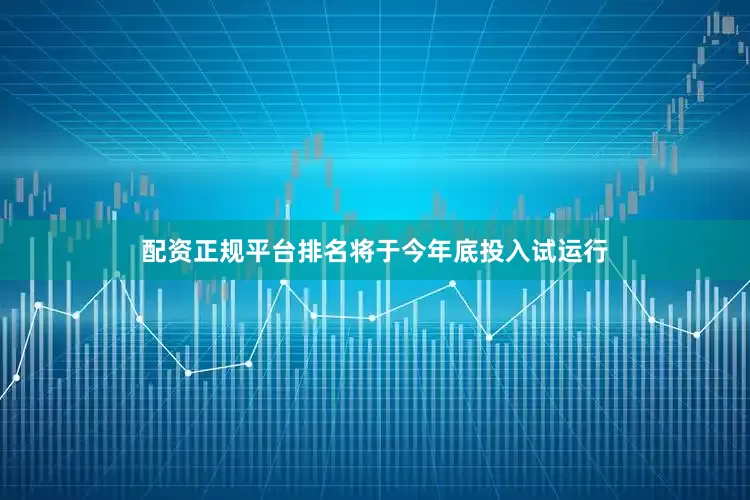2025 年 6 月 28 日,德黑兰的晨雾尚未散尽,伊朗国家烈士陵园已笼罩在肃穆的氛围中。一场特殊的国葬在此举行,送别在以伊冲突中丧生的 14 名顶尖核科学家与 4 名高级军事指挥官,其中包括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・萨拉米、应急指挥部司令吴拉姆 - 阿里・拉希德等关键人物。这场葬礼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,更成为观察伊朗国家战略、国际博弈与国内政治生态的棱镜。
一、血火淬炼的 “烈士名录”
以色列在 6 月 13 日发动的空袭行动,以 “灭门式” 精准打击伊朗核设施与军事指挥系统,导致萨拉米等高层将领与 14 名核科学家在睡梦中殒命。这些遇难者中,萨拉米作为革命卫队灵魂人物,曾主导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战争布局;而核科学家团队则掌握着铀浓缩、离心机研发等核心技术,被以色列视为 “核计划的大脑”。以色列驻法国大使乔书亚・扎尔卡直言,此次暗杀使伊朗核计划 “倒退数年”,甚至可能 “彻底终结”。
展开剩余72%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定性为 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”,并迅速启动国葬筹备。6 月 26 日,萨拉米的家乡戈勒派耶甘率先举行私人葬礼,数千民众手持国旗与逝者肖像,高呼 “复仇” 口号;两天后的德黑兰国葬,则由总统佩泽希齐扬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政要亲自主持,全国下半旗致哀。这种 “地方悼念 - 国家仪式” 的双重架构,既延续了什叶派 “殉道者崇拜” 的宗教传统,也通过媒体直播将悲痛转化为全民共识。
二、国葬背后的战略叙事
伊朗将国葬塑造为 “抵抗轴心” 的象征仪式。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停火声明中强调,以色列妄图摧毁核设施、引发内乱的阴谋 “彻底失败”,反而自身重要设施遭受重创。这种叙事在国葬中得到强化:革命卫队仪仗队护送覆盖国旗的灵柩缓缓前行,宗教领袖在悼词中援引《古兰经》章节,将科学家与指挥官并称为 “为信仰与国家牺牲的烈士”。
此举暗含多重战略意图:首先,通过抬高遇难者的国家英雄地位,凝聚因经济制裁与社会分裂产生的国内矛盾。2025 年伊朗通胀率超 30%,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声浪渐起,国葬成为转移焦点、重塑凝聚力的政治工具。其次,向国际社会传递 “核计划不可逆转” 的信号。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・伊斯拉米在葬礼前表态,伊朗已启动 “重建预案”,确保核生产 “不会中断”。这种强硬姿态既是对以色列的威慑,也是对美国谈判立场的施压 —— 尽管美国国防部评估空袭仅使核计划 “延迟数月”,但伊朗仍坚持将解除制裁作为谈判前提。
三、国际博弈的涟漪效应
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与伊朗的国葬仪式,将中东地缘博弈推向新的临界点。美国虽未直接参战,但通过情报支持与战略默许深度介入。特朗普政府宣称伊朗核设施 “已被彻底摧毁”,而五角大楼内部报告却显示核心部件尚存,这种矛盾折射出美伊谈判的胶着状态。欧盟则呼吁克制,担忧冲突升级将破坏地区稳定,但其对伊朗的 “建设性模糊” 政策在制裁与对话间摇摆不定。
地区盟友的反应同样耐人寻味。沙特在沙伊关系缓和后保持谨慎中立,既谴责暴力行为,又避免公开支持伊朗;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则通过声明与集会声援伊朗,试图重塑 “抵抗轴心” 的凝聚力。值得注意的是,阿联酋在 2020 年法赫里扎德遇刺时曾谴责暗杀,但此次保持沉默,凸显其在 “亲以” 与 “防伊” 间的战略权衡。
四、历史镜鉴与未来挑战
此次国葬与 2020 年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遇刺后的葬礼形成鲜明对比。彼时伊朗通过立法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,并加速铀浓缩活动;而此次事件后,伊朗选择 “哀悼与重建并重” 的策略,既强化军事报复的威慑,又通过总统公开信释放 “抵抗胜利” 的信号。这种转变反映出伊朗在经济制裁与政权存续压力下的务实考量 —— 既要维护核计划的象征性价值,又需避免全面战争引发国内崩溃。
然而,伊朗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依然严峻。以色列的 “斩首行动” 暴露其防空系统的技术代差,而国内强硬派与务实派的分歧可能削弱政策连贯性。若无法在核谈判与经济复苏间找到平衡,国葬所凝聚的短暂共识或将被持续的民生困境消解。正如革命卫队在葬礼上宣读的誓言:“烈士的鲜血将浇灌胜利之花”,但如何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战略优势,仍是伊朗必须破解的难题。
德黑兰的葬礼钟声渐息,而中东的烽烟未散。这场国葬不仅是对逝者的致敬,更是伊朗向世界宣告:在核野心与生存危机的夹缝中,这个国家将以血与火书写不屈的抗争叙事。
发布于:安徽省万生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